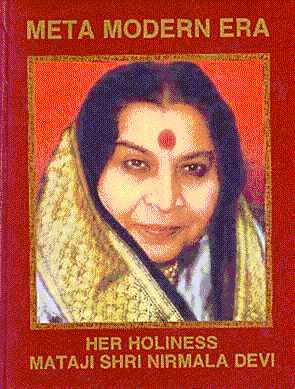 |
超越現代 Meta Modern Era 錫呂.瑪塔吉.涅瑪娜.德維 (Shri Mataji Nirmala Devi)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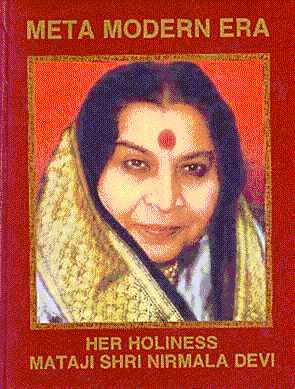 |
超越現代 Meta Modern Era 錫呂.瑪塔吉.涅瑪娜.德維 (Shri Mataji Nirmala Devi)著 |
( 續 •第一章 )
此所以那些知道真理的人,許多時會逃避其他人,因為他無法調整他的洞見,來迎合那些最流行、最成功或最為時尚的那些思維投射。他站在絕對真理的基石上,他知道在那些理性的現代主義者的混亂背後,有一個絕對真理的國度。他知道不能被「自我」(ego) 局限的用理性來達到這個真理,而是要依靠我們的昇進。這不是憑空想像的,而是我們的「靈」( Spirit) 或魂 ( Soul ) 的實際經驗。那「靈」像一個車輪轉動的軸心。如果我們的注意力移到我們存在的輪那不斷轉動的軸心,我們便會被那「靈」啟發,那是內在平安的泉源,使我們到達一種完全平靜和具有對真我知識的境界。
可是如果我們的知覺仍然附著那自我,那輪的邊緣,那我們生活中的正常過程,仍會繼續運作,但我們只是生活在一個相對的水平,圍繞著我們的混亂當中。除了這自我的局限以外,所有那些欲望、期待、思想積集等也會影響和扭曲我們的意識。只達至表面的身體或精神的感官,產生緊張、壓力、筋疲力竭。相反,「靈」的內在特性將我們提昇得高於所有人為的,不真實的混亂,直達到純粹的真理、使我們散發平安到外在的環境。這不是勉強可以得到或用錢買到的。這是通過一個活生生的進化過程,自然而然地實現的。在我們昇進了之後,那不穩定和相對的意識便與無所不在的上天意識合一。因為通過實現自覺,那「靈」便知道了自己,而且是自我放射,絕對自信和自滿自足的。我們可以說那「靈」是完全的覺知,因此能高度察知自己的本質。
我在上面說過,那「靈」的智性,就像獨一無二的光,向四周散發,無論它到達哪裡,都會繼續的散發出光,不會有那種對反的反應,產生反作用。那來自靈體之光的意識能夠知覺,改變及創造。那「靈」的智性因此不簡單是因,或是果,而是因與果的結合。它不是主動,也不是被動。因此它不去宰制,也不去受命於人。它有一種內在的特性,能有效的行動。我們可以說:「它在,故它做。」
以太陽的光芒為例,那光芒照在樹上,就產生葉綠素。這過程不用任何有意或精神的投射。這種知道何者為真和去作事的能力是內在於靈體之中。放在大地母親上的種子會自動發芽,因為種子和大地母親都有內在的性質來產生這個效果。只是簡單的根據萬物的本性,那些活生生的事物自然而然地發生作用。每一樣事物都自然的成為,從潛能上來說是的那樣事物。
相反,精神的過程沒有那種自然放射的行動,因為它不是扎根於那所有事物的創造泉源,即那靈體之上。精神的過程無論做甚麼都是有意的、自我中心的,被思想積集所制約和強迫的。它是一種直線的運動,不會向後看或左右觀察。最後它不能支持它自己,因為它裡面沒有真理的力量,因此會反彈,傷害那原先的觀念,這是在一開始之時從沒有想到的。
希特勒便是這方面極端的例子,憑著一己的理性,他確信那些猶太人正在毀滅德國。因此他提出一個理論,說德國人是高貴的雅利安人,是最高的民族,而那些猶太人則是低等的民族。這是個理性的理論,卻毫不接近真理。那些德國人將別人放在毒氣室裡殺死,還享受這種景象,這些德國人怎會是最高等的民族?被毒氣殺害的人之中,不少還是十分可愛的兒童。對那些沒有被理性蒙蔽了雙眼的人來說,很明顯,只有最低等、最原始的種族才會這樣做。那個理性建構的最後結果,是希特勒自身的毀滅。因為他那種消滅猶太人的念頭是一種精神的投射,而所有精神的投射,最後都會反擊自己。當一個人超越了一己自我意識的有限範圍,超越了一個人精神投射的自然界限時,便會發生對反的作用。它便會反擊那最初的作事者,像一支縳了繩在後面的箭一樣,雖然向前射,卻會反彈回來,傷害那持弓的人。
即使在表面世俗的層面,我們的日常生活也告訴我們,不要盲目的讓理性帶領,而是要監察著它,將它限制在適當的領域。
理性有它的用處,但我們不要走向極端,無視過度理性所帶來的後果。令人驚訝的是,由於自我的瘋狂力量,沒有甚麼人能夠從經驗中汲取教訓。許多因為他們的投射而受苦的人來找我,即使在我嘗試醫治他們的時候,他們還要為毀滅他們的東西辯解,說:「我這樣做又怎麼樣?這樣做有甚麼不對?有甚麼不對?有甚麼不對?」這好像變成了現代人的咒語或口頭襌。但如果我們願意從生活經驗中學習,而不是重覆的念誦:「有甚麼不對?有甚麼不對?有甚麼不對?」我們便能找出中道的實踐智慧,避免走向極端。通過實踐,我們可以將理性限制在清楚的界限,保持我們的平衡。這樣,我們便可保持較高的警覺,不會受到傷害,也肯定不會毀滅自己和其他的人。
如果一個人能夠內省,並且在心裡謙卑的說:「我不知何謂真理,但我會找尋真理。」這樣終有一天,這種謙遜會獲得回報,那個人便會得到他的昇進。得到了昇進以後,那個人的注意力便會在中央,不左也不右。也就是說,他的注意力不會受他過去的思想積集所操控,也不會受他那野心勃勃的自我傾向所支配。這樣一個平衡的人便很適合獲得他的自覺,這樣他便會知道真理的絕對形式。
說了這麼多關於理性的問題,以及如何通過靈性之光來知道真理,以避免現代主義的混亂,就說到這裡為止了。現代又叫做黑暗時代,或鬥爭期,產生梵文所說的‘bhranti’,即混亂。現代的另一被預言過的詛咒是人們很容易走向罪惡和毀滅性的行為。也有人預言說,在現代,那些當權的人會容許及鼓勵這種行為,因為他們感到很合適。他們不會找尋毀滅的根源(即現代主義的核心)以解決那些社會問題,他們只會提供斬件和短期的解決方案,這樣反而會造成更多無法解決的問題。舉個例說,有一位辛普森先生,他是著名的足球明星,被控謀殺他的太太。結果美國的雜誌出現了幾篇文章,說不應有婚姻和家庭制度。美國社會只有二百年的歷史,但在這幾年間,他們做盡一切來毀滅他們的社會。他們有甚麼權利去評論社會和婚姻制度,去毀滅其他有深遠傳統的社會?但這只是治標不治本,把社會的根基摧毀而已。政府已不再關心人民的真正福祉,權力將落在謀取經濟利益的人手中,他們透過報章和其他具說服力的媒體,像電視等,來討好人民最低下、最自私的欲望,以收買他們的選票。我們在現代所看見的,超出了任何的預言和想像力。
智性謙卑的最佳例子,不在那些知識分子的建構,而是在那些心裡有著謙卑的,深沉的詩人,那些簡單的,以繪畫為對上主奉獻的藝術家。在他們的精神投射中,他們看見上主以自己形象所創造的世界。這些謙遜的人的自然創作是大自然和上天的永恆反映。他們的畫,他們畫筆的每一筆,都充滿繁茂和喜樂,像散發香氣的蓮花那樣,打開我們的心。他們的作品散發出一種獨特的、寧靜的啟示力。也有一些所謂「樸質」和「鄉土」的畫作,模仿這種藝術的風格。
可惜在現代,我們沒有大師級的作品。我們最多只能抄襲過去的大師,或高價買賣他們的作品,當作一種投資。在現代,我們已經放棄了永恆藝術的觀念,而相信所謂現代藝術。那所謂現代藝術是很主觀的,只能被那個藝術家自己了解,或者要他加以大量評注,才能說服我們的理性,相信他的創作多麼有價值。然後總是有些評論家,他們對於永恆或靈體沒有知覺,他們會將那些偽裝成高貴的荒謬捧上青天,完全違反所有良好和正常的感官。
當然,現代藝術如果是從無形無象的靈所放射出來的,也可以是一種十分進化的表現。它打破了傳統藝術的線條和形相,創造了無形相的實體,充滿光及透切的意義。但要實現那個潛質,那個藝術家要是一個得到自覺的靈,才能畫出那無形的喜樂,表達那放射出無形的及自然而然的音樂的靈體。這樣的藝術不需要評注和討論。只有詩人才能描述它。一個像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一個進化得很高的靈和先知,才能又畫又寫,將他的所見描述於詩句之中。這種詩人的想像力,能達到所有美麗的高峰,也只有一個得到自覺的靈才能欣賞和享受。所有那些進化得很高的靈,無論他是坐在一個簡陋的村莊為女神織造披肩,或者是在唱誦讚頌上天永恆的詩句,又或者是在演奏著上天的音樂,他們全都是創造者神聖的漣漪。他們有時不被了解,他們有時被批評為無知、盲目的人,但他們是為了自己,為了那些具有上天知識,能夠明白他們所描寫的世界的人而唱,而奏出他們的音樂。
要與這種洞見溝通,用不著現代那種庸俗和感官的暗示,來表達藝術家的衝動。如果那是純潔的藝術,那它自身便是令人震憾和使人極之喜樂的。以至如果你看見或聽見那樣純潔的藝術作品,所有思維都會停頓,親身經歷到喜樂的美妙,這喜樂是那個藝術家創作那作品時,他內心所感受到的。這種對何謂真的精微感覺是對一個得到自覺的靈的恩賜,與那些只由理性所創造的作品截然不同。
那些屬於知識分子的評論家,他們沒有這種精微的知覺,他們甚至連一條線都畫不出來,他們只是用那自我取向的有限理性加以把弄,卻因此而給予他們自由,去批評那些新進的藝術家,扼殺他們的作品,傷害和麻痺他們的感受能力。舉個例說,有一天我在電視上聽到一首極為美妙的管弦樂曲,作者是一個八十歲的英國老太太。那首樂曲非常美麗動聽,可是在第二天,報紙上出現了半版的批評,貶低這首優秀的作品。自此之後,那位作曲家就銷聲匿跡了。
在這些所謂高深的評論背後的推動力是甚麼?是否出於嫉妒?是否由於那些人沒有創作的才能,轉而學習這種批評的技倆?問題是我們無法在學校裡學會怎樣去欣賞真正的藝術。這不僅是個思維上明白的問題,而是一種內在的靈性經驗。那些論證家只是在思維的層面來欣賞,其實是很危險的,因為那樣做會忽略,甚至毀滅了那些真的藝術,而將那些無意義的、陳腐的,甚至最終來說具破壞性的東西賦予人為的吸引力和價值。他們為甚麼要批評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品味,他們為甚麼要用他們訓練有素的攻擊言辭來誤導他人呢?同理,那些具有犀利言辭的記者,在訪問那些非常謙卑和有智慧的人時,會用他們滔滔不絕的言辭來扼殺被訪者的觀念。
如果我們觀察現代主義的作品,便會看見,現代主義基本上只產生那些淺薄和混亂的作品,只產生在思維上批評的精益求精。幸好所有這些問題都有一個內在的解決方法。如果所有偉大的藝術家都消失了,結果會怎麼樣呢?這已經在事實上發生了,那些藝術家由於他們的創造力和他們內在感受能力而飽受批評,使他們都飽受驚怕而靜默下來。這時,那對反律便會發生作用,那些評論家也會消失,因為還有誰可以給他們評論呢?他們便要開始互相批評,這正是目前所發生的,因為那些評論家就像被編定了程序的機器一樣,他們不會停止旋轉,攪拌出他們永無休止的批評。分析是一種有害的態度,就好像把一個美麗和帶著芳香的花朵,弄得片片碎。
現代主義的問題是,它不斷毀滅和取代自身的建構。且讓我們再看一個對反律的好例子。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侵略別的國家被認為是很時髦的事。猖狂的掠奪是流行和普遍的。到了二十世紀,流行的是對別的國家有「開明」的興趣。但對反律可確定一點,就是無論新的趨勢是甚麼,那鐘擺還是會擺回來的。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由於西方國家過去那些盲目的觀念,在對反律之下,已直接為西方帶來許多問題。
在這幾個世紀裡,理性通過以白人為媒介而達到了它的高峰。那些白種人從理性思維出發,洐生出一種線性的想法,認為其他膚色的人種,不是由上帝創造出來的。他們相信神一定是白種的,而且最可能是盎格魯•撒克遜種。神將不同的膚色賦予其他人類,但基於這種特殊的理性,或者說是對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的合理化,他們殺了數以百萬計的人,掠奪他們的土地,並把其人民做為奴隸。結果在北美洲,我們已找不到一個自由地以傳統方式生活的印第安人,因為他們已被鎖在那些侵略者「慷慨」地留給他們的保護區內。我們要到博物館裡才看見圖畫中的印第安人。他們帶著印第安人的頭飾,但很奇怪,畫的是盎格魯.撒克遜人。
感謝上帝,天命使哥倫布去了美洲,而且把他留在那裡,而不是他認為他要去的印度。否則,印度境內的「有色」人種,包括印度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西藏、尼泊爾、亞富汗,和其他許多類似的國家,還有他們遠古和深厚的文化,都會被那些優越感情結作祟的征服者,全數加以蹂躪和破壞。那些西班牙的鬥牛者,他們對人類文化所造的貢獻,只是製造了那些所謂安詳寧靜的天主教墓地。但要補償哥倫布所錯失的,那偉大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從英國來到了印度,沒有人邀請過他們。他們盡其所能的消滅印度深厚的智慧傳統,然後這些人光榮的離去。他們平安的離開了印度,但這偉大的國家已災難性的一分為二,最後分成三個不同的部分,埋下了暴力和毀滅的種子。
今天,侵略的帝國儘管已完全的土崩瓦解,但那「聯合帝國」背後那種個人主義和殖民地主義的理性理論,還是持續下去的,而且內裡有同樣的、威力很大的對反律的火焰在燃燒著。大英帝國正面臨不同組成部分的壓力,他們不僅互相攻擊,以保護他們的個人主義,而且不惜用暴力來毀滅對方。在北愛爾蘭,每一天都有人因為維護或破壞殖民主義的殘餘而被殺。過不了多久,平靜的倫敦又會受到恐怖分子炸彈的威脅,這種情況到最近和平談判開始了才停止。也沒有人知道,這戰爭前的平靜能維持多久。
現在我們嘗試弄清楚,這種思維建構的對反律如何運作。當那些盎格魯.撒克遜人忙於侵略特別是在美洲的「次等」文化和「有色」人種時,他們的自我便發展起來,以致他們對現實完全的盲目,他們開始認為他們那種狂妄和不人道的殘酷行為,是絕對正常和恰當的。根據他們那種理性的邏輯,他們真的是稱心滿意,他們侵略了整個世界,粉碎了所有「次等」的民族,使他們順從。現在可以舒舒服服坐下來,享受傲慢的果實。當然,對反律又開始表現了出來。特別是在美國,開始繁榮起來。儘管在美國革命及反對殖民主義時有過偉大的理想,那些美國人慢慢的成為奢侈品的奴隸,成為他們自己的自我主義的犧牲品。隨著時間的消逝,他們視那些非盎格.撒克遜人種,那些猶太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俄羅斯人如同次等的民族,將那些人當作外族人來欺侮。至於那片原屬印第安人的土地,他們就當作是他們自己的。可能有許多人出於宗教的熱誠,說這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說他們是上帝賜福的選民,來做這毀滅這些印第安人的工作,因為他們太「原始」了,沒有白皮膚,而上帝肯定是有白皮膚的。
現在那些白人都有美麗的都市,都市裡面有美麗的房屋和花園。所有那些本來是別人所有的繁茂的森林和肥沃的土地,現在都是屬於他們的了,他們成為這些土地和上面一切生產的合法主人。那些人被殺戮、被驅逐,只是因為他們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這樣他們就完了。再沒有人想起他們或為他們擔憂,因為通過那可以自圓其說的理性,所有事情都可以合理的解釋。
但不幸的是,這種侵略實際上沒有停止。根據對反律的自然定律,當你侵略其他人,毀滅其他人時,這種侵略會返過頭來,向你侵略。那些曾自誇為個人主義者、理性主義者,有著很高文化的人,那個盎格魯.撒克遜族和其他曾狂妄地侵略殖民地的民族,由於對反律的作用,已第一批的走到集體自我毀滅的危機。他們集體的沉迷於毒品和濫用藥物。這些毒品都從哥倫比亞、波利維亞等地方運來。在那裡,那些原先是美洲本土居民和土地所有者的印第安人還在,但受到忽視,處於窮困的谷底。他們跑到高山上,來逃避那些白人的攻擊。我們不該驚訝,他們當日的藏身之所,都成了對反律運作的核心。那些最厲害的毒品,像「冰」( Crack),就是在這兩個國家製造的,然後由那些美國人自願的走私進美國,以毒害他們的國人。而這兩個國家本地的人卻不會沈迷於這種殺人的毒品。他們只是製造毒品,而那些像西班牙人等的白人,把這些毒品出口到華盛頓去。在美國,這種毒癮不限於任何一個城市,或任何一個類別的人。它們傳播的範圍很大,你可以在邁亞米、三藩市或洛杉磯的繁忙街頭找到死於毒品的人。就像擅入美洲的白人對印第安人無盡的殺戮已造成一種慣性,現在他們要不斷的殺害。他們那殺戮的技倆對印第安人已用了許久,現在也要好好的鍛鍊一下,好像練習打網球一樣,保持著好身手。
今天,他們甚至搶劫和殺害那些比他們富裕的人。當這些發達國家越來越富裕,由於對反律的另一個運作,他們也製造出數量越來越多的和越來越複雜的黑幫。他們利用綁架富人來謀財,他們所到之處,都散佈了貪污和悲慘。這個黑幫大帝國是無法控制的,而他們卻能控制政府和那些政客。
現在西方世界將錢看得如此重要,錢變成是每個在現代主義這不幸的星座之下出生的人,頭上的一條索命繩。但我們要明白,所有這些強盜和黑幫,只是依對反律而有的一種反平衡力而已。
然而盜竊的並不限於罪犯的階層。在美國,每一個階層的人,從上而下都沉迷於貪污、盜竊和巧取豪奪,要不然就是靜靜的忍受這些無賴和流氓的暴行。他們不但繁榮昌盛,並且建立了幫派的王國。暴力已達到驚人的地步,如果有誰要到美國旅行,就不該戴手錶或珠寶,甚至連結婚戒指也不能戴。
這種對正常人性價值的侵蝕和緩慢的毀滅在美國到達了可怕的頂峰。人性的價值本是永恆的正法,如果一個人在傳統的價值觀下長大,他會自然而然的尊敬這種正法。但在美國,人們將酗酒和吸食毒品視為當然。甚至在那些精英分子、知識分子的派對,他們談的都是毒品,就好像過去他們談論法國的葡萄酒一樣。
更嚴重的是性泛濫。因為人們陶醉在他們所謂的自由裡,就失去了修養、自然的莊重謹慎和自制能力。越來越多報告指出,他們甚至沉迷於虐待他們的子女。即使動物的母親,也比這些殘暴的母親對他們的子女好。這完全是超出人類的想像,也不知要怎樣責備它才好。但在這種以「好玩」為包裝的暴力文化下,他們似乎集體地對正常的道德價值都免疫了。這種「可口可樂」文化充滿了鬼節式的慶祝,充斥了毒品的迪士高,庸俗和不雅的音樂。試問一個可憐又「原始」的印度占星師,如何能預言到現代這個墮落和不道德的世界呢。
最近,聽說在美國,有二百名兒童被警察虐待,而警察應該是值得信任和保護兒童的人。在現代,兒童受的苦最可怕,對這些被虐待的兒童來說,那種苦處可能比死在毒氣室裡更甚,因為他們還要背著這種童年時的創傷,繼續活下去。在加拿大,許多天主教的神父毀了許多天真無邪的小孩子。最近,我很震驚的得知,奧地利天主教會最高層的神父,被控侵犯兒童。他穿的是紅色的教衣,我真希望將他放在鬥牛場裡,讓幾頭凶狠的公牛收拾他。甚至那些兒童本身也覺得,要過這樣一種被蹂躪的生活,不如早一點死去。不久之前,有個很年輕的女孩子,被父母逼著去主演一部有關惡魔附身的恐怖片,當她長大成人時便自殺了。
也許這種喪盡天良的人,這種傷害兒童純真的罪惡行為,是過去預言都沒有提到的,因此那些西方人不大相信印度的預言。他們強烈的認為,古代印度的占星師並沒有很強的洞察力。那麼諾查丹瑪斯 ( Nostradamus 諾斯特拉達穆斯 ) 又怎樣?似乎由於古代的預言家無法容忍和連繫到這種可怕的事實,就沒有人相信這些事情會發生,直至到了現在,在這個黑暗時代 ( Kali Yuga ) 的最低點,大家才肯相信。
當我在報章上讀到在美國虐待兒童的消息,我真的非常震驚。有位美國女士坐在我旁邊,她也要飛往美國,她驚訝為甚麼我這樣震驚。她說:「我一點都不感到奇怪,因為如果你理智的想一想,這種事情在這個世界每天都發生,只是美國的傳媒不怕把這種新聞印出來。」這種個人的理性辯解,已走到了它的邏輯結論,造成一種集體的想法,去逃避作內在的反省。這種掉以輕心、不負責任的想法避開了一個十分危險的、關乎人性的問題。同時完全忽視了長期以來受到尊重的價值和傳統文化。如果林肯還在世,他對這樣的社會會有甚麼反應?感謝上天,這些偉大的靈都得到安息了。只有我們這些現代人,才會因現代的煽情報導而感到震驚。這些煽情的報導都是那些反應敏捷的人做出來的,他們想方設法使現代的傳媒感到震憾,結果造成了血癌。
今天,在這些發達國家之中,似乎沒有人是安全的,因為每個人都忙於用他們的理性來將暴力合理化,就好像在飛機上跟我談話的美國女士一樣。而且,傳媒不斷將暴力當做娛樂,那些電影、影視中心都是這類片子,令大眾都對這種事情不再感到羞恥或缺乏人性。我們還可以看見,人們寡廉鮮恥的利用所有可怕的事情來大賺其錢,來證明他們有創作力。他們無暇再管其他的事。即使是那些已有足夠的錢的人,他們還是貪得無厭,希望賺得更多,用盡一切欺詐的方法,從那些比他們有錢的人身上,甚至從比他們窮困的人身上賺錢。然而,對一個來自不同文化的人來說,談論大眾濫用藥物,特別是酗酒,是一種罪惡。飲酒在盎格魯.撒克遜人及歐洲的民族中,已被抬舉到如同偉大的宗教活動。他們從不討論這種宗教,到底它是好的還是壞的。飲酒是神聖的,那些不喝酒的人是怪異的。甚至是他們社會的發言人,那些知識分子和所謂高級官員,喝醉了以後,再沒有誰堪稱健全的典範,更遑論智慧了。相反,他們集體地被一桶桶的啤酒,烈酒和各種葡萄酒,以及一切使人酒醉的東西所迷住。當然,他們發明了千百種不同的辯解,甚至透過媒體,非常出色的辯護這種自我毀滅,和使人神智不清的習慣。不幸的是,這種喝酒文化,現在已散播到一些在傳統上,把喝酒當作瘟疫般來逃避的社會。
有一次,我剛好和朋友住在一起,她的丈夫是政府高級官員,但他們兩個人都是酒徒。我很驚訝的看到,他們家裡簡直是一蹋胡塗,裡面甚麼都沒有,堆滿的盡是喝酒派對的東西。他們甚至沒有一張備用的毛毯給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和高層人士,只會為酗酒文化寫一部聖經。要拜那些沒有原則的國家,和那些市場學上的天才所賜,使這些人朝向毀滅的路上前進。
那些法國人,從腐壞的葡萄汁和芝士中建立了一個高度複雜的文化。現在他們覺得奇怪,為甚麼他們的葡萄變成白色,且不再發酵;為甚麼全國都患肝病和有蜥蜴似的皮膚,這是否對反律作用於他們身上?是否又是對反律使他們經歷經濟衰退的震憾?還有另外一個對反律在起作用。在希拉克先生( Mr.Chirac ) 的大選以後,報章上刊登了一篇很長的政府官員的名單,他們都被拘捕以及監禁。事緣他們自己喝很多酒,身邊又有一群酒鬼,憑他們,薪水是怎樣支付得來的?而且他們許多人都喜歡養情婦,還把他們的情婦派任法國政府高層的工作。
似乎沒有人知道,為甚麼西方國家如此吹噓他們的經濟和經濟學,但經濟蕭條卻會像疾病一樣的蔓延。其背後微妙的原因是他們所喝的啤酒、葡萄酒和烈酒。這些都使他們失去真正的自由,將他們工作和享受純潔生活的力量和願望都消耗怠盡。在他們的生活中,有一項即時的危機,如果他們不能在酒吧喝酒,或者沒有了一天假期,就可能由此走上不歸路。耶穌說過,酒使人放縱。我要說,在現代,酒使得經濟不景氣。
甚至在教堂,在領聖餐時,他們給予那崇拜者腐敗的、發酵過的酒,當做他們靈性上的得益。他們的解釋是,耶穌在迦南時,為一場婚宴,把水變成了酒。當然,你可以利用生命能量,將水變成葡萄汁,但這些生命能量怎會創造一些令你喪失意識,把你下拉到次人類的層次的事物呢?邏輯上說,怎會有一釀就好的酒呢?酒一定要讓它腐化很久,才是最好的。然而,對於現代那些真正的酒徒來說,沒有伏特加,就沒有真正的聖餐。伏特加是俄國一種最烈的酒,因為對於一個酒徒來說,他已習慣了強烈的酒精,普通的葡萄酒並不能帶來那種精神效果。在英語之中,靈 ( Spirit ) 這個字可以解作酒精,可以解作亡靈,也可以解作真我 ( Atma),即全能的神的反映。
我真不明白他們為甚麼要利用耶穌基督,來支持他們飲用那發酵過的葡萄酒,因為這是與一個人的知覺背道而馳的。相反,耶穌基督來到世上,是希望幫助我們昇進,高於那普通人類的理性知覺。耶穌基督在迦南一下子就把「酒」做出來了,他沒有讓這些葡萄汁發酵。所有那些葡萄酒和甜酒都是經過發酵的,即使是法國聖本篤會修士所釀的「賜福」甜酒,也是經過發酵的。而那最好的酒是最臭的,是由那千年以前腐爛得很的葡萄做的。那些有幸嚐到這些酒的人,喝了一口之後會說:「噢,天啊!」沒錯,那味道地球上絕對聞不到,而那些喝醉酒的人,比豬還臭,而那些不喝酒的人,站在他們附近也受不了。可是在那些發達國家,每一個人都似乎在追求這種境界。他們似乎已經失去了嗅覺。他們的身體發出臭味,因為在法國,人們已不時興洗澡。法國浴的意思變成是在酒精上灑點香水,然後感到法國文化是至高無上的。
在一個大型的招待會中,一個人得和超過五百人握手。一旦他們開始喝酒,就會一直喝到晚上十點十一點,儘管招待會是由六時開始,打算在八時結束的。這是他們唯一不看手錶的時候。可憐男主人和女主人還要在他們離去時站在門口幾個鐘頭,沒吃沒喝,看著賓客慢慢的失去意識,還要和他們逐個握手。那些賓客還大力的捏和扭你的手,直至你的手也感到麻木。可憐主人一直忙著和新來到的客人握手,連坐下來的喝杯水或喝杯茶的時間也沒有,便要和那些不勝酒力的人道別。除了回教國家男人不許和女士握手之外,他們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方式,女主人也不能拒絕。這只是西方社會多種消遣方式的一端。當然,人們會將這種瘋狂的行為合理化,說這根本不是現代的,而是傳統的,因此就一定是好的。但如果我們有一點常識,便可看出這完全是浪費金錢和精力。在那些場合,你很少會聽見他們談及工作或其他有意義的事情,談的大部分是醜聞和其他無謂的閒話。有一天如果你要主辦這種接待會,那就特別要小心那些法國人,他們一定要親吻女主人的左右兩頰,男的就有時親,有時不親。今天傳染病之多,我認為至少我們要廢除這項「傳統」。
所有這些東西背後有更嚴肅的一面。這樣的消耗酒精,會嚴重浪費大量個人和國家的資源。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應作一個調查,看看所作的花費有多少,那些酒會和日常喝的帶來多少正面的效果,然後提交每一個國家的國會討論。因為那些發達國家花費國民收入的一大部分來使國民保持在不清醒的狀態,實在是愚蠢的表現。而那些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國家,若被誘惑而追隨西方國家的步伐,這樣的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在外交關係上,也是不可原諒的。甚至連印度的東道主和侍酒人員,也個個穿著燕尾禮服,打著蝴蝶領帶,熟知所有蘇格蘭威士忌和苦艾酒。
我們必須承認,英國真的精於喝酒的「傳統」。在英國,在任何一個村莊,最美最顯眼的建築物,一定是酒館。他們說:「這是村莊的社交中心。」可是那些在酒館中的人,不是已經喝醉了,就是準備去大醉一番,通常他們也會很快喝醉。在與任何人碰面以前,他們必先喝一杯,否則就很難交朋友。他們甚至為親友死亡而大喝香檳。他們有些人所持的理由是說,只有這樣才能把情感拋開。酒喝得越多,人們彼此就越冷漠,接著他們便開始失去人際關係的道德感。在這一群屬於「飲酒文化」的人之中,有一個新近的例子,有個八十歲的老太太,竟給自己十八歲的孫子寫情信,然後這封信還刊登在紙章首頁,好像是發生了甚麼大事一樣。這種對倫理關係的混淆不清,直接來自飲酒。飲酒令道德感遲鈍,因為他們長期喝的其實是毒藥,結果造成麻痺,漸漸摧毀人類彼此之間的道德感。可是這些國家還是對酒精極之尊崇。我在加拿大遇見了一位哲學博士,他寫了一編很複雜的論文,討論如何透過酒精,達到「靈性上的昇進」,因而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
酒精對人類知覺和行為的影響,遠遠不是提昇意識水平和改善人類生活的道德。我在我的工作中發現,很難給那些習慣喝很多酒的人自覺。有些人可能真誠的求道,但卻因失望而厭倦,才喝起酒來的。如果不是因為得到自覺,而是因為其他原因,他們戒除了喝酒的習慣的話,他們多數會馬上感染其他的惡習,像賭博、追逐女人或男人,或者是吸毒。因為酒精摧毀了一個人對崇高的生活、對更高的意識、對靈性和道德昇進的基本願望和能力,也使他喪失了那種平衡。
在西方社會,人們喝酒就好像在進行宗教儀式。我認為這方面他們就與塔法里教派 ( Rastafarians ) 沒有分別。塔法里教派將吸毒視為他們其中一種宗教儀式,他們很少不在被附身的狀態之中。今日大部分的罪惡,都是在醉酒的狀態下犯下的,或者是為了酒癮或毒癮。但在這個「現代之後」的時代 ( Meta-Modern Era ),那些得到覺醒的人,將可免除所有這類的強制、毀滅性的習慣。這個時代現在已經開始了。我知道有許多人不會放棄這種殺人於無形的酒癮,這種酒癮已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如果你不準備「飲料」 ( drinks ) 的話,就無法請人吃晚飯。我所指的飲料就是「酒精」,你得去查查字典。維多利亞女王有個亦僕亦友的侍從,叫約翰.布朗,他相信如果一個男人不喝酒,沒有這個缺點,就算不上是男子漢。
在馬拉塔語 (Marathi) 中有句話說:「如果酒瓶從一個門進入,[ 財富女神] 拉希什米便會從另一個門離去。」如果一個人神智不清,你怎能期望他對妻子,對子女,以至對社會國家有責任感呢?他無法正常工作,無法享受一個正常人的人際關係和責任。他的注意力受到扭曲,他的肝會失去功能,而他會變成一個脾氣暴躁的人。
由一個「喝酒的人」,可推廣至整個現代西方社會。社會上的不景氣,是他們更大的困難。但除了不景氣是他們的飲酒文化創造出來之外,還有就是一向支持與增進他們道德和社會關係的傳統價值系統,正在完全的腐蝕中。看起來,去參加酒會,到酒館喝酒,是種很古老的習俗,雖然如此,這一切都一定在現代變本加厲。連法國作家如莫泊桑、莫里埃和塞拉,都將酗酒拿來開玩笑。在現代,甚麼都沒有界限。這似乎就是現代人的真正成就,超越了一切禮法的界限,對生命完全沒有尊重。
在這種社會,人們的感知力不斷被削弱,不僅是由於酒精,還由於他們受到知識分子的疲勞轟炸,還有那些粗淺的感官刺激。現在的傳媒已精於此道,他們不斷強化這種感官的刺激,從那些專欄作家膚淺的閒話和陳腐的醜聞,到虛假和無恥的頭條新聞,到色情、暴力和恐怖的充斥,不斷重複對正常人類智慧和責任感的侮辱。這股潮流不受控制,在不知不覺間,已潛入如電視等我們熟悉和信賴的媒介,悄悄的進入我們的家裡。
也許最糟糕的,是看見這些社會中,婦女被人們模塑成的那個樣子。自尊、莊重和溫柔,這些性質,在世界任何地方,本來會很自然的與母親結合在一起,但在西方社會,這些都被視為毫無用處、毫無價值的。也許那些婦女還是要在頸上掛著十字架,經常要上教堂去,但她們仍然要很傲慢,無禮且毫不莊重,或很富侵略性,否則她們便被視為弱者,不夠上進。在這種扭曲的理性看來,也許傳統的女性被視為是軟弱的,但在要進入上帝的國度時,她會被視為明智的。
看見西方這種情況,我可以了解為甚麼穆罕默德要求婦女遮蓋她們的面孔和身子。因為他是個先知,他一定是看到了未來的西方婦女,她們完全沒有廉恥,用盡一切方法來吸引別人的注意力。在這樣的社會,那些乏善可陳的時裝設計師和髮型師,生意最為興隆。他們也扼殺了美麗的愛情,因為人們開始因為某種髮型或某種時裝而墮入戀愛。可是到了第二天,他們的愛情便落空了,因為他們所愛的人,已換了髮型,或穿了另一套衣服。
現在,衣衫襤褸的款式及邋遢的扮相最為流行,人們稱它為「便裝」或「入時」的造型。可憐那些髮型師和時裝設計要榨空心思,才發明光頭的髮型,和用緞帶做衣服,將身體暴露得最多為止。
從理性的角度看,西方的婦女,若果是聰明的話,就必須很富侵略性,特別是那些職業婦女或女政客。在政治圈子裡,她必須像吸血鬼一樣可怕。在社交生活中,她們不僅要令人望而生畏,還要有迷人的魅力,可與那些蹬著眼看人而從來不笑的模特兒相比,或者可與那些像妓女般往上爬才有出頭的明星相比。
為了要有吸引力(吸引甚麼?吸引誰?),她們一定要顯露身裁,裸露大腿,似乎要引來色狼強姦。她們是那樣的木無表情。分析到底,她們的邏輯好像要說,在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如果不能吸引別人來強姦她們(這樣吸引每一個人是很危險的),又怎會有人來宣傳她們是迷人的女子?又怎能「開發她們的本錢」,並得到回報呢?穆罕默德一定是預見了這樣的婦女,她們完全不尊重自己的貞潔和尊嚴,像牲畜一樣,為此,穆罕默德才規定婦女要穿得樸素大方。這些婦女不知道,大部分牲畜都用四條腿站立,而不是用兩條腿站立來自我展示。
西方社會的另一個詛咒是害怕變老。為甚麼男男女女都迫切的要看來年輕?因為理性告訴他們,又或者說是那些廣告告訴他們的,如果一個人老了,沒有人會看你,也沒有人會理你。於是為了換來陌生人下流的目光,她們願意將美麗的貞潔放棄。社會上若充斥了這種膚淺的想法,這個社會就不會進步。
這個社會的成員,他們不尊重自己身體的隱私,也不尊重自己的年齡,對一個外來文化的健全訪客來說,他們的個人及社會行為,使他們看來就像接受人工虛偽與愚昧的白痴一樣。
端莊、謙遜、尊嚴和智慧是傳統社會的自然產物,是建基在正法的永恆價值之上的。但是在西方,這些價值都受到攻擊,甚至遭受低貶,因為人們已不再尊重簡單、自然和正常的事物。這象徵著自然和內在的衰落,人工化的抬頭,像塑膠這種物質,已悄悄的進入所有物料,滲入西方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塑膠對維持健康的生活,並沒有甚麼幫助。經常使用的話,會引起各種皮膚的問題,甚至是呼吸系統的問題,因為塑膠不是一種天然的材料。
甚至那自負為聰明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他們曾在美洲虐殺印第安人,指他們為原始),現在已非常墮落,他們無法明白,為甚麼他們有那麼多無法醫治的神經失常和精神病。他們還把這些疾病帶到亞洲去。他們到那些落後的國家,花錢購買肉慾的沉迷。因為侵犯兒童在他們的國家是犯罪的行為,他們便到泰國或其他東方國家幹那可怕的犯罪勾當。如果他們的行為得到智慧的指引,有著謙卑和對他人的尊重,他們的生活便會有平衡,不會那麼容易患上身體或精神上的疾病。
在以後的章節,我會詳細討論,人們的道德生活和他們的身體和精神狀況二者之間的密切關係。我還會討論到廣泛的物質主義,首先是機械化、繼而是自動化,最後是電腦化對西方社會造成的影響,同時會指出,當工業發展達至極端時,會產生些甚麼問題。我們可以看見,問題的根源在於,人的精神投射沒有內建的智慧來規限它,所產生出來的事物也沒有平衡。它不斷的自我支持,直至那對反律發生作用,最後使它崩潰。這些都是現在那些所謂「發達」國家所發生的問題。理性似乎是對現代的一種詛咒,因為理性創造了這個現代社會,然後為它辯解,但最後這個社會的衰亡,也是由於這種不受限制的理性。
( 待續 )